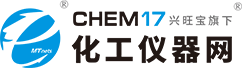生物制能的利用及現狀
生物質是指通過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各種有機體,包括所有的動植物和微生物。而所謂生物質能(biomass
energy ),就是太陽能以化學能形式貯存在生物質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質為載體的能量。它直接或間接地來源于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轉化為常規的固態、液態和氣態燃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一種可再生能源,同時也是*一種可再生的碳源。生物質能的原始能量來源于太陽,所以從廣義上講,生物質能是太陽能的一種表現形式。很多國家都在積極研究和開發利用生物質能。生物質能蘊藏在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等可以生長的有機物中,它是由太陽能轉化而來的。有機物中除礦物燃料以外的所有來源于動植物的能源物質均屬于生物質能,通常包括木材、及森林廢棄物、農業廢棄物、水生植物、油料植物、城市和工業有機廢棄物、動物糞便等。地球上的生物質能資源較為豐富,而且是一種無害的能源。地球每年經光合作用產生的物質有1730億噸,其中蘊含的能量相當于*能源消耗總量的10-20倍,利用率不到3%。
2006年(丙戌年)底全國已經建設農村戶用沼氣池1870萬口,生活污水凈化沼氣池14萬處,畜禽養殖場和工業廢水沼氣工程2,000多處,年產沼氣約90億立方米,為近8000萬農村人口提供了生活燃料。
中國已經開發出多種固定床和流化床氣化爐,以秸稈、木屑、稻殼、樹枝為原料生產燃氣。2006年用于木材和農副產品烘干的有800多臺,村鎮級秸稈氣化集中供氣系統近600處,年生產生物質燃氣2,000萬立方米。
發展生物質能源重在解決“五難”
面對性的減少化石能源消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形勢,利用生物質能資源生產可替代化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產品,已成為我國應對氣候變暖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國家出臺了具體的補貼措施,并且規劃到2015年,生物質能發電將達1300萬千瓦的目標。然而受原料收集難、政策補貼不到位等難題,生物質能源產業的發展規模和水平遠遠低于風能、太陽能的利用。如何發揮生物質能企業的生產積極性,盡快解決這些難題,為此,記者采訪了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生物質專委會秘書長肖明松,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秦世平教授,以及可再生能源學會生物質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袁振宏。
一難:認識不夠
生物質能源正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境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秦世平研究員開門見山地告訴本刊記者:“要說重要,在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質能源是zui重要的,但相比而言,它的產業化程度,發展規模都是zui差的。這其中有一些客觀原因,也有一些屬于認識問題。
生物質能源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四點,秦世平介紹:*,我國是地少人多的國家,農林剩余物、城市垃圾等廢棄物是生物質資源的主要來源,以往農民處理秸稈大多是一把火點著,城市垃圾多是填埋,但廢棄物的處理是個剛性需求,隨著國家對CO2的排放限制的提高,生物質的能源化利用成為更為先進和有效的方法;第二,我國化石能源短缺,其中液體燃料是zui缺少的,而液體燃料只有利用生物質可以轉化;第三,生物質能的各個生產階段都是可以人為干預的,而風能、太陽能只能靠天吃飯,發電必須配合調峰,而生物質能源則不需要,甚至可以為其他能源提供調峰;第四,生物質原料需要收集,這樣能夠增加農民收入,刺激當地消費,可以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一個2500萬~3000萬千瓦的電廠,在原料收集階段農民獲得的實惠約有五六千萬元。“三農”問題解決好了,對于整個社會發展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客觀上發展規模受限以外,秦世平認為:對生物質能的認識各不相同,對其投資的額度,與地方的GDP增長是不相符的,資源的分散性導致生物質能源在一地的投資,zui多也就2億多;這在某些政府官員那來看,生物質能源有點像“雞肋”,有呢吃不飽,丟了又有點可惜,并且地方政府還要幫助協調農民利益、禁燒等“麻煩事”。由此導致生物質能源整體項目規模較小,技術投入不足,盡管它是利國利農的好事,卻處于發展欠佳的尷尬地位。
可再生能源學會生物質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袁振宏也在里向記者表示,相比于煤炭、石油、天然氣這些傳統能源,生物質能源在技術上的投入顯然要低得多。對于生物質能源發展,首先要從上層統一思想,提高對生物質能源重要性的認識,并要在技術上加大投入。
二難:補貼門檻過高
對生物質能源的支持,國家采取了多種補貼手段。但補貼門檻過高,手續繁瑣、先墊付后補貼也困擾著不少企業。財政部財建[2008]735號文件規定,企業注冊資本金要在1000萬元以上,年消耗秸稈量要在1萬噸以上,才有條件獲得140元/噸的補助。對此,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生物質專委會秘書長肖明松認為:1000萬元的注冊資金,是國家考慮防范企業經營風險時的必要手段,這對大企業無所謂,但對一些中小公司則很難達到。而1萬噸秸稈的年消耗量,需要相當規模的貯存場地,由此帶來的火災隱患,成本增加問題也是企業不得不考慮的事情。事實上,如果擴大鼓勵面的話,三五千噸也是適用的。受制于這些現實難題,財政部的萬噸補貼政策遭遇落地難。
而參與國家補貼政策制定的秦世平對此解釋說,國家制訂政策的初衷并不鼓勵生物質能源企業因陋就簡,遍地開花,而是鼓勵企業專門從事生物質能源,培養骨干型企業,這就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一萬噸的廠子,固定資產就大概需要400萬元,加上流動資金,1000萬元并不算多。而萬噸規模在能源化利用上,剛稱得上有點規模,只要是同一個業主,生產點可以分散,如果規模太小,補貼監管成本也太高。對于補貼方式上,秦世平承認存在一定缺陷,整個機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門、技術部門的參與。制度怎樣更有利于監管,公平公開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而該行業的快速發展,補貼政策功不可沒,但不能因為出現一些問題,因噎廢食,取消這個補貼政策,那將會對剛剛起步的生物質能源化利用產業造成重大的打擊。因為國家補貼不僅僅是提供資金,還表明國家對該行業的支持態度,對企業和投資具有強力的引導作用。
除此之外,固定電價也是補貼的重要一塊。生物質發電是0.75元/度,垃圾和沼氣發電是0.65元/度。增值稅實行即征即退,所得稅按銷售收入的90%來計算。袁振宏則指出政府鼓勵生產,生產完了沒有銷路,這個產業還是發展不起來。所以生產者和用戶兩頭都要鼓勵,為企業開拓市場。產業發展了國家才有政策,反過來不給政策,企業也難有市場。
三難:布局不好要吃虧
到底企業要建多大產能的好?秦世平經常碰到有企業負責人向他請教。
“沒有,只有的,適合的就是的。比如蘇南地區每人只有幾分地,那就沒法收,這些地方就沒法建大廠,但東北墾區就比較適合建大型電廠,有條件上規模,成本才越低,效益才越高。一定要因地制宜。密集地區可以建氣化發電,做成型燃料,不一定去建發電廠。”
肖明松也建議企業要多方考慮,合理布局,否則很容易陷入發展困局。建生物質能電廠首先要考慮可持續發展,原料分散,就需要分散性利用,要考慮水資源、電力、人文環境是不是可以支撐這個項目。
四難:成本價格難控
受耕作制度的限制,我國農村土地高度分散,從資源的收集儲存運輸帶來很大不利因素,在后續的環節上會放大很多倍。“有些人認為收集半徑的擴大就是多一個油錢,實際上運輸工具、人力成本都不一樣。”秦世平解釋說,“裝機容量3萬千瓦的生物質電廠,一年大概需要25萬-30萬噸秸稈,按我國戶均10畝耕地計算,需要大約20萬農戶來完成,那么收購時你要帶秤,光開票都需要20萬張。還要一個個裝車,不能實現的機械化。”
肖明松也非常理解企業的苦楚。“生物質能源要依賴農業,資源掌握在老百姓手里,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好,*隨行就市。如果收集半徑過大,需要農民花費大量時間收集、運輸,那農民就會要求按外出打工時計算人力成本,如此一來,企業為原料支出的成本就會大大提高。如果企業堅持不抬價,就可能造成企業吃不飽,縮量生產,影響經濟效益。每度電原料成本如果超出一定范圍,無論怎么發電都是賠錢。加上人工費用近年來的快速增加,成本成了扼住企業脖子的一道枷鎖。
“所以準備入行的企業首先要考慮的是原料資源的可獲得性,如果不成熟千萬不要貿然進入。”肖明松認為地方政府可以進行協調,比如利用示范效應,鼓勵農民種植秸稈作物,做好企業加農戶的結合,平衡好企業和農戶之間的利益。
五難:技術投入小
“我國的生物質能源技術與國外有一定的差距,但目前的技術加上國家的補貼可以維持產業化經營。技術進步永無止境,國外的技術、設備成本太高并不一定適合我們,轎車科技水平高,但要是去農田就不如拖拉機。”秦世平笑著向記者打了個比方。科研部門每年都在做前端的研究,力度并不大。從實驗室到田間再到工業企業的規模化生產,技術的創新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企業可以一邊生產一邊進行探索。
“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有些研究成果與生產有些脫節,并沒有轉化為生產力,推向社會。”肖明松說,一方面技術部門因缺少資金,無法進行規模化生產,另一方面為了盡可能多地收回技術成本,企業有意拉長新技術向市場投放的周期。“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化的市場,如果抱著老的技術不放,一旦有新技術投放市場,企業始終面臨著效率低下,zui終難以維持。”
“生物質能源的技術投入還很小,從宏觀方面來說,現有能源還沒有用盡。壟斷企業控制著部分能源的終端,也限制了中小企業的技術投入。中石油若投入生物質能源,生產乙醇汽油很容易,因為燃料乙醇按標準要求添加到汽油里形成乙醇汽油,整個產業鏈他們可以控制,別人加不進去。當大能源還能夠持續的時候,就不會在生物質能源上下太大的力氣。”此外,石油、煤炭,天然氣價格有一個聯動關系,當他們的價格逼近生物質能源的產品價格時,企業就會有更多的利潤,當化石能源資源枯竭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生物質能源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
 您好, 歡迎來到化工儀器網
您好, 歡迎來到化工儀器網